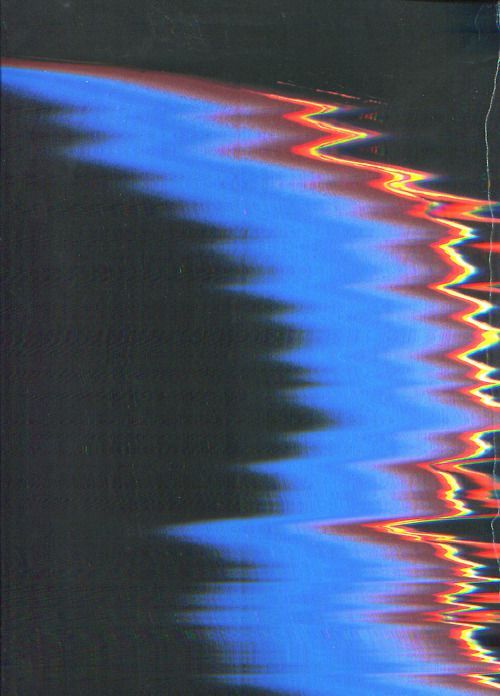乐园(14)
快速目录
一些碎碎念:
很久到底是用原版的萨蒂里孔作标题还是用中文译名。相较于国产的讽刺中产小资的爱情神话,我更喜欢费里尼呈现出的古希腊色欲神话,如果涉及的角色不是小皮匠而是别的男人,或许真能编排出一段更随便更淫荡的“萨蒂里孔”,可惜有小皮匠,所以还是要矜持一点,小资一点,现代一点,只能演一出隔靴搔痒的“爱情神话”了。
爱情神话(上)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改机票瞒着所有人提早一天结束了在欧洲的旅行,也许没心情,也许是太孤独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坐了十几个钟头的飞机后没有选择回家,而是在机场临时订了一个在地旅行团。我乘坐的航班在浦东中转,拿行李又比普通乘客快很多,所以等那队叽叽喳喳的上海中老年伙伴走近时,已靠在出口的栏杆旁等了足有二十多分钟。
“勿好意思啊导游,我们刚刚拿行李出了点小插曲。”一个穿着黑色皮夹克、头发灰白的白胖中年男人微微欠身,一脸疲惫地朝我点头,“我姓白”他指指我手边写着“白先生,上海”的泡沫牌子,边说,他的一双手一边忙不迭地从身后三个女人那边接过已经使用过的飞机票,像二十多年前的公交车售票员一样,收拢完了一沓票子就折好了塞进自己腰前的小包里。身后某一个烫着大卷的时髦女人用上海话嗲声嗲气地拧着腰,对男人说道:“白老师啊,我渴啦!”
“我也渴啦!”另一个扎着辫子妆容朴素许多的女人一甩头发,也跟着出声,摊开手伸过去,她的语气自然,底气也是很足的,手伸到男人的鼻子底下。
“哦哦。我这里有水。”男人应声道。扶着眼镜,殷勤地从自己的小挎包里掏出两瓶迷你装的矿泉水,眼睛却偷偷看向旁边唯一没有出声的紫发女人,等着她也开口要水,与其服务别人他似乎更青睐服务这位性格安静的女士。谁知那女人故意避开他的眼睛抱着胸微微侧过身,眺望起远处的出租车车流。男人失落下来,应付同伴的话愈加敷衍。哦!哦哟哟,这是在干什么?这四个人什么关系?我好像闻到了抓马的味道。同行的另外两个男人明显在年纪上要大上一圈,明明是三男三女的组合,却搭伴站在离她们两步远的地方,眼睛里闪着神采——三个女人,两瓶水,怎么分呢?怎么分就怎么偏心啊……他们对被女人们围追堵截的同伴可不报有同情之心,反而带着不可言说的吃味,立在旁边聚精会神、竖起耳朵,观察那边四个人的动静。胖男人刚要递水的手临了收回来,偏头看向我,眼睛一亮。我正歪着脑袋看他们的热闹,冷不丁又被叫过去。
“导游小姐啊,你这个水要不现在就发了吧,我们路上也好休息休息嘛。”白老师斜着眼瞧向我的脚边,那里正放着一个黄色的半透明塑料袋,里边鼓鼓囊囊的装了好几瓶农夫山泉。他说要分水,其实也只是想从袋子里拿出来一瓶而已,讨来的这瓶水是专门替紫发女人留的。
“哎……白老师。”我把接机牌放倒,拎起袋子里取出水交给男人,卖弄起现学的上海话念了一遍称呼,笑道:“我不是导游哦,你搞错人啦。导游去上厕所了,我帮她看东西而已。”
男人呆住,一脸糗。“啊?”紫发女人扭瓶盖的手也顿住。
我连忙安慰说:“没关系,没关系,本来就是给你们准备的饮料。”
女人哪还敢喝。等导游本人湿着手一路小跑过来才解除误会。
“我就讲现在噶许多导游哪能派头嘎大啦,一身名牌!也就白老师个老实头会弄糊涂咯。”时髦女人上下打量我一番,从包里取出一副与我同品牌的太阳镜,展开,架到鼻梁上,扬起下巴对我笑着点头。得她提醒另外两个女人才注意起我的着装,一个不以为意,一个一脸探究。至于白老师,从头到脚他只认出来一件Burberry。“白老师!”娇滴滴的上海话响起,我掏出水转身递给旁边看热闹的男人们两瓶。身后,纤长的粉色美甲捏着瓶身推到白老师胸前,“我刚做了指甲,伐好拧盖子嘛。”
两个老男人飞速交换过眼神,电光火石之间已完成了一场男人间的加密通话。我挑起眉毛,其中一个扎着意式领巾模样挺有派头的男人朝我道谢时还顺道抛了个媚眼。哎哟喂,这上海男人。另一个耷拉着眼皮看着没精打采的山羊胡老头面相挺老实,小声说了句口音颇重的:“谢谢。”眼珠子只瞟到我的手部高度,甚至没费力再朝上抬抬,好似刚才听八卦活灵活现的劲头只是我的错觉。
导游举着小旗招呼众人上小巴。我是最后一个上车的,正巧听到前边的花哨老头和山羊老头嚼耳朵,嘀咕说:“啊是?我老早讲咯,噶趟出来肯定好白相!”笑得意味深长,旅途还没开始说的自然不是闽南风光。两人前后脚地坐到第一排。
我一钻进车,后座的白老师就探身出来好奇道:“哎,小姑娘,你怎么上我们的车啊。”
“白老师,我和你们是一个团的呀。”我也笑嘻嘻。本来我是准备在车里混半天的,现在也来劲了。
“啊?老白你不是说报的精品小团嘛?”朴素女人对着男人一瞪。
导游急忙解释:“我们是精品小团,最高可容纳八位贵宾哦。”
“白老师!”时髦女人合起粉饼盖,皱眉抱怨。
“老白!”
“好好好,不要吵不要吵。”白老师拖着嗓音,摇头晃脑眯着眼睛滑手机,显然在找自己订团的信息,确认完详情里确实有一行“可能拼团”的小字,“唉”了一声才瘪着嘴收起手机,等导游说拼团可以再返还一笔费用后,彻底没声儿了。
此时车尾基本已被占领,女人一个座,身边的手提包也占一个座,一人一边,三足鼎立,可怜的白老师没挨着任何一个的身,独自一人坐在末尾享受一整排。三个女人故作平淡地看向我,我起了坏心思,故意把目光瞄准了最后一排,推起行李箱,果然见到其中一个人已开始默默收拾提包放到腿上让出邻座的位置,只等我走得更近就要出声将我拦下。她们到底没这个机会了。
“来来来,小姑娘。”第一排的花哨老头及时叫住我,“不要和他们掺和,我们年轻人坐前边。前排不容易晕车。”
车尾的白老师松了口气,心情轻松下来忍不住笑着斗嘴道:“老乌侬面皮真个老噢,搭人家小姑娘坐一道!好意思啊,侬看看皮匠,出来一趟老老实实。”
老乌搂过座椅靠背,扭头翻了个白眼回呛:“侬先顾好自家再讲!导游姐姐,麻烦给他一个晕车袋,等会儿别吐在我们车子里了。脏死了。”
“侬勿要乱讲啊,我带好晕车药的!”
导游考虑了一下,给了白老师五个塑料袋。后车有人想吐就问他拿。
大家素不相识,没道理挨坐在一起。老乌的过道对面坐了导游,我则坐在导游的后排。山羊胡老头站起身帮我一起把行李箱挂好,他直着身子时与我蹬上高跟鞋差不多高,搭完手重新坐回过道的另一边,隐晦地瞄了我好几眼。“谢谢。”我笑道。当我把太阳镜推到头顶,他的目光从我的黑色高跟靴上转开,爬过小腿和风衣衣摆,跃上平放在大腿跟的双手,着重在无名指的第三节指节处搜寻,搜寻可能存在的被指环勒过的痕迹,最后上移到侧脸。看一眼,假装系安全带,然后再看一眼。以为我不知道。
好看吧?哼,男人哪有老实的哦。看就看呗,我已补好全妆,王天润临走前交给我的银行卡也没浪费——为了泄愤,我在苏黎世重新置办了一整套堪称豪华的行头,衣服裤子鞋子帽子眼镜耳环……乃至发卡,都是今年秋季最贵最新的款式。那叫一个爽刷。索性买其他东西都容易露馅,武文陆搞不清楚我有哪些新衣服,所以穿在身上的才是最保险的。随便打扮一下,还是漂亮得不行。果然只有人嫌物贵,贵物可不挑人。
我也扭过头瞧他,越过滑下的茶色镜片故意对他眨眨眼睛。老式眼镜后的大小眼微微睁大,似乎没想到我会是这么个反应,立时不自在地低下脑袋假装在包里翻找什么。听白老师叫他皮匠,前头还要加个“小”字,小皮匠,小皮匠,一点都不庄重。小皮匠可不小啦,看着比林彧还大一些呢,也不知道姓什么?收回视线,半道正好和老乌撞上,他笑眯眯的,也不知道躲在一旁观察了我和皮匠多久,等我看向他才翘起二郎腿,侧身问我:
“小姐怎么称呼啊?”
“姓高。”我说。
“高小姐是本地人吧?”
“咦,你怎么知道?”
“你能听出我是上海人,我当然也能听出你是福建人哦。自己是不觉得自己讲话有口音。”老乌清了清喉咙,“我以前有个老同学家里就是漳州的,大学毕业和他一起在福建做过两年生意,后面生意赔了就回上海了。我会说点闽南话还会唱闽南语的歌呢。”
“哎哟老乌,勿要唱啦。”末尾的白老师唉声抱怨,在车子驶入郊区颠簸了几下后,脸真的开始发白,刚已经斜躺在座位上闭目养神,他拍拍前坐的朴素女人,说:“蓓蓓,晕车药你啊吃完了,给我一下,我有点顶不住了。”
老乌不乐意了:“做啥啦?我唱歌勿好听啊?”
皮匠也劝道:“勿是勿好听,天天屏牢刘德华唱,耳朵也听出老茧来了噢!”
“侬搭啥腔?我唱刘德华?”老乌将矛头对准身后的皮匠说道,“唱歌老点给我一杯忘情水的不是你吗?唱得认真的不得了。”
“老乌,看不出来,你们两个还去 ktv 唱歌呐!我还以为你已经成精了不用排解寂寞了哦。老实讲,有新花头了伐?还是皮匠在谈朋友?”时髦女人搭话道。
“我啥辰光点过忘情水。”皮匠脸红起来,踢了前座的靠垫一脚,“好了好了,我不要同你讲话了。回去坐好,再同侬讲闲话我都要晕车了。”
老乌指着时髦女人笑道:“啊呀,格洛瑞亚,你要去的话下次再约我就叫上你一起。蓬荜生辉啊。”
“帅哥有伐啦?”格洛瑞亚娇矜地扬起下巴,“假使还是㑚几位老甲鱼,我才勿去嘞!”
“有是有,当然有帅哥,就是年纪也都有点大了。要实在不行,我把白老师也拉上嘛。伊相貌是没我登样,不过才华搭够呀,这点小缺憾补补嘛正好,侬讲是勿啦?”
格洛瑞亚哼了一声,不接话。
老乌对皮匠挤挤眼睛,坏笑着对我点头。
“老乌。”我收起笑容把眼镜推到额顶,一脸严肃地对他说,“你别说,我现在越看你越觉得你长得很像一个老牌的电视明星呢。”
“真的呀?是谁啊?”老乌自恋地摸摸脸颊,乐得眼睛都看不见了,兴致勃地凑过身来追问。
我摸着下巴作沉思状。
白老师微弱的声音从车后传来:“像啥啦?像阿庆!闲话模子。”在座几个上海人登时哄堂大笑,格洛瑞亚笑得最大声,最矜持的紫发女人也捂着嘴偷笑。我不知他们讲的是谁,和回头的导游面面相觑。
老乌说:“我像阿庆,侬就是阿德。正好侬儿子也是做咖啡的。”他转过头问我,“到底像谁啊?”
“嗯……”我摇头,“现在看看又不像啦。我再想想吧,等会儿告诉你。”
“咦!你怎么还卖关子啦?”
“人家高小姐就是说你——”白老师刚开口,突然神色一变拎起腿上的塑料袋,弯腰躲到靠背后。只听他呕了两声,塑料袋刺啦刺啦响着。皮匠重重叹了口气拉开车窗,鼻子嘴巴移到风口。一群人争先恐后、手忙脚乱扒拉着打开自己那边的窗户,让着惊天一呕扰没了闲聊的兴致,瞬间作鸟兽散。
“不好意思啊。”白老师虚弱地说,被四面八方灌进车厢的凉风又冻得打了个响亮的喷嚏。前座的紫发女人抽出面纸巾递给他,“谢谢侬啊,李小姐。”白老师不好意思地擦着嘴,女人重新挪回窗边,时不时关切地回头望望他,有两次都对上眼了偏又立即把视线飘走。
我倚在窗边假装看风景,其实一直从座椅缝隙里偷看。心满意足了才转过身子,正巧对面皮匠也偷看完,就要扭身坐正,面面相觑,一时都有些尴尬。我这个人厚脸皮惯了,再难堪也不会红脸,眼镜一盖,只当什么都没发生。车子又走了二十分钟才到目的地。
“小心脚下。”老乌跟着导游率先下车候在门旁,像老黑白电影里的绅士一样挺胸抬头主动伸出胳膊让我去扶。我自然乐得配合,嘻嘻哈哈下了车。
“来,你也小心。景区离医院还是有点距离的。”老乌将胳膊伸给紧跟着下来的皮匠。皮匠觑他一眼,也不反驳,从善如流地扶上老友胳膊下了车,两人插着兜晃到一边,和我一起溜到树下乘凉。
“怎么走啦?我是病号你也不扶扶我啊!”车边白老师抓着扶手侧身下台阶,只有两脚踩在同一平面时才肯向下踏一步,身形很是笨拙。老乌摆摆手当作回应,三人又看见白老师一脸虚弱,强打精神站在车边给三位女士作人形扶手。
“啧。哎。”皮匠一言难尽地摇头。
老乌戏谑道:“怎么,你当齐人之福这么好享的啦。”
“白老师到底喜欢哪个啊?”我小声说,“我觉得他的态度已经很明显啦。他明明就是喜欢——”
“诶!小高,男女之间这种事不好说出来的,说出来了还有什么看头啊?”老乌连忙打断,“土楼我老老早来过好几次了,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最美的风景是人’。我们是来追连续剧的,是不是啊皮匠?”老乌用肩膀撞撞友人。
皮匠笑了,没说话。满眼狡黠,这哪是个老实人。
“倒是你啊,出来玩怎么还穿高跟的鞋子。”老乌朝我的双腿努努嘴。
我瞪大眼睛说:“别小看我,我能穿着高跟鞋跑步的。”
“哦哟这么厉害。”老乌思索了下很正经地说,“没事,跑坏了叫小皮匠给你修。手艺好的嘞,不开玩笑,他老爸就是个皮匠,有家族传承的,最会修高跟鞋了。”
皮匠立刻变脸说:“别听他的。我这两天打烊了,不做生意的。”
“哦——”我拖长语调,哼,修完不付钱,不就不算做生意啦?等皮匠不自在地低下头仍盯着他的额头看,“放心吧,我和导游说过了,走到大榕树我就歇下来,她拜托我帮忙点好甜水等你们过来喝呢。”
远处的白老师叫道:“欸!你们还走不走啦!哪有一下车就躲阴头里边的,老同志应该身先士卒不要带坏年轻人!”他以手搭棚撑在眉毛上,皱着脸望向我们,在被阳光照成白色的水泥地上,活像个原地站岗的企鹅。李小姐她们则像群春游的小学生一样围在导游身边,已经走到十几米外了。
“你又急死了!”老乌骂道,走出树荫跟上队伍。留下我和皮匠慢慢缀在后边。白老师发给我们一人一个鲜红色的带着旅行社 logo的鸭舌帽,老乌很嫌弃,就连白老师也没戴,只有皮匠默默戴上了。
小皮匠离我半臂远,我存心逗他,偷偷靠近问道:“皮匠叔叔,你姓什么呀?我也不好跟着他们一起叫你小皮匠小皮匠的,多不礼貌。”
“啊?别别别!别叫我叔叔。”皮匠听到我的声音,不知想到什么身体一抖,赶忙抬头朝我摆手,嘴里磕绊了一下,“你就和他们一样,就叫我皮匠好了。我不介意的。”满脸惊恐……我说什么了,至于吗?
“诶你小——”我伸手要去拉他,谁知皮匠躲得更厉害,展示出与年龄不符的灵活身段,一个抢步和前边不知为何忽然脚步放缓的老乌撞到一起。两个老头差点一块儿栽到草丛里去,好在旁边的游客眼疾手快扶了一把。老乌和皮匠立时互相埋怨起来。我哭笑不得地合上嘴巴。
走到榕树我便依着计划停了,找个空位坐下,兜售纪念品的小贩凑上来催促我买点什么,我在藤编的篮子里挑出把扇子,正好用来赶飞虫。石桥对岸,白老师的灰头发、老乌的鹅黄色领巾,还有小皮匠大红色的鸭舌帽,被人群掩埋,很快就消失在在络绎不绝的游客动线之中。看了一会儿财经新闻,又玩了会儿消消乐小游戏,我预计他们边听讲解边游览至少得花个四十分钟,快结束时导游会给我发微信,所以抬起头看到李小姐和格洛瑞亚搀着白老师已走到脸前,有些措手不及。
“这是怎么啦?要不要叫救护车啊。”我惊道,起身把座位让给他们。白老师的面色比在车上还差,捧着肚子,脑袋磕在木桌边沿,一口一口倒吸着凉气。
“没事的,他就是中暑了。”李小姐说。从包里取出一瓶没开动的水,扭开瓶盖塞进男人手里,叫他漱漱口。格洛瑞亚掏出一只粉蓝色的电动风扇,启动电源,放在男人的通红的脸颊旁,给他扇风。我识趣走开到旁边的铺子里点了饮料,一直候在里边,等商家制作完才端着托盘走出,这时导游和老乌一行也已经结束参观聚在桌边,各自找位置坐了。
两个女人还围在原地,蓓蓓嫌弃地看了她们一眼,来到我跟前帮忙接过东西。“谢谢你啊,高小姐。”她说。
老乌甩着自己那顶簇新的红帽子扇风:“怎么样啊白老师,好点没有?刚进门什么东西都没看到呢,多可惜啊。不过好歹有两个丫鬟伺候你,这趟也不算白来了。”
白老师唉声叹气地解开衬衫领子,吹着小风往嘴里灌了几口水,一副活过来了的模样,斜眼笑道:“你羡慕啊?”有力气贫嘴,说明确实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老乌不理他,对一旁的格洛瑞亚说:“格洛瑞亚,你的小风扇给我也吹吹呢。”
“不要。”女人头也不抬一口回绝。
“你看看!”老乌一脸不忿,“厚此薄彼嘛。”
“好啦好啦,我给你扇。”我从包里掏出刚买的旅游折扇,坐到老乌旁边,装模作样给他扇了两下风。谁知这老头大喇喇享受了一会儿眼睛一转,捧起一碗汤水起身走到后边的石栏杆旁,说:“哎,算咯,我老乌有甜汤喝就知足了。嗯,真好喝!”
老乌一走,露出原先被自己挡住的满头大汗的皮匠。他谨慎地看我一眼,我顺势挪过去坐到他的旁边,腿肉撞到他的腿侧,接了老乌的话茬说:“行吧,老乌没福气,那我给小皮匠扇扇。”摇扇子的手腕距离他的手不过几厘米之远,我顺势前倾身子歪在桌上,让他能透过衣领看见锁骨前坠摇摇的那颗钻石项链。皮匠撞进我半挑衅半兴味的笑容中,表情居然显出无奈来。“怎么样,舒不舒服啊?”我手上不停,殷勤地送去凉风。
三个女人耳朵一动,不约而同地越过中间啜饮清水的白老师,互相交换眼神。
皮匠深吸一口气,也不知是不是职业习惯,他看人喜欢压着下巴,耷拉眉毛,一双圆眼睛从镜片上边望人。无辜是无辜,但也显得整个人又苍老又没精气神。三个女人看他这样子,不约而同地摇摇头,否定了内心刚刚升起的猜想。不会吧,他?又把眼睛移到后边整理领巾的老乌身上,点点头。嗯,他倒是还有点可能。
什么?时刻关注女伴的白老师被她们的反应搞得莫名其妙,不论怎么眨眼都没对上女同志们的信号。皮匠低下头喝水,也不知道到底看没看懂。站在树下的老乌看得分明,嘿嘿笑着问:“皮匠啊,现在是什么季节啦?”
“秋末了。”皮匠说。
“哦,我还以为是春天呢。”
白老师看老乌像在看神经病。
“秋天好啊。有腔调,我就喜欢秋天。”格洛瑞亚说,捧着手忧郁地蹙起眉毛。
我点头道:“秋天多好,收获的季节嘛,不冷不热,生机勃勃的,多有意思。”闻言,李小姐探究地看向我。小皮匠不多话,放下空碗接过我的扇子合起来放在手边,态度暧昧,没让我继续献殷情,但也没把那支廉价扇子还回来。
“什么乱七八糟的。快点喝吧,我看你们也要中暑了。高小姐,我没说你。”白老师端起甜水招呼起来,“我这碗你们谁喝?我喝不了太甜的。蓓蓓你要不要喝?老乌你话最多,给你润润喉了。”
“你啊。你!”老乌走过来接过汤碗,恨铁不成钢地指着白老师,“朽木!懂伐啦?”
“搭错神经啦你。”白老师一甩胳膊将他轰走。“你不是朽木,索菲亚罗兰干嘛和你分手?”
“索菲亚罗兰?”我机敏地接收到新讯息,疑惑道。
皮匠小声解释:“老乌的前女友。”
“好耳熟啊,是我想的那个索菲亚罗兰吗?意大利那个。”
皮匠点头。
“哇!索菲亚罗兰啊,老乌,她比你大二十多岁吧,你怎么追到手的?”我扭头。
白老师对我的反应大吃一惊急忙说:“啊?不是……那是索菲亚罗兰诶!你怎么会真的相信索菲亚罗兰是他前女友的!高小姐,你不要信他,他吹牛的呀!”
老乌也颇感意外,他说的这段往事一向是被邻居们当成玩笑话来调侃,第一次有人当真,脸上的忧郁一扫而空,挺起腰杆走过来,一屁股挤开皮匠坐在我俩中间,兴高采烈地对我说:“那可说来话长了。话说89 年的时候,我才二十岁出头,到法国去留学,在巴黎综合理工大学读书,第二年放春假,我闲着无聊跑到罗马去旅游——”
老乌手指蘸水,在桌上画了个图案,说是罗马的形状,就要给我讲方位地形,刚花了个十字这时导游却挥着小旗子插嘴道:“各位贵宾,我们要启程到下一个目的地去咯!”
“没办法,时间不巧。等会儿有机会我再和你聊。”老乌抹去水渍遗憾起身。
一行人上了车,除了小皮匠以外所有人都坐回了原位。皮匠改坐到老乌的旁边。
“你干嘛?”老乌一脸莫名,想了想,坏笑着调侃说,“哦,我知道了。皮匠,平常我看侬面皮老得唻,什么女人和高跟鞋的道理,嘴巴嘎老,搞了半日天全是理论知识,真的遇到穿Jimmychoo的女人侬又戆脱了!别害羞啊,人家都不害羞。有啥好怕个啦?”
“是是是,侬老法师,啥侬最懂。”皮匠系好安全带就闭眼躺在靠背上,帽子一歪盖在脸上,一副要睡觉的样子。
“阴阳怪气。我懒得搭侬烦了。让一让,我去小高噶搭坐,大家清爽。”老乌还心心念念着自己那个才开了个头的故事,上车后就想趁路途空挡讲完,推推皮匠哪知推不动他,旁边人的两条腿踩在踏板上,膝盖顶着前座,挤也挤不出去。这下可好,想出来都没办法。老乌扒开皮匠的帽子埋怨道:“才几点啊就装睡……现在是啥意思啦?把我关拉里厢啊?”
“开车了,赶紧坐好,勿要乱动。”皮匠纹丝不动,见老乌还在坚持,举起手向导游报告说,“导游,老乌不肯坐,他有事情要宣布。”
“乌先生,怎么了嘛?我们要发车了,安全起见您赶紧坐下吧,有事等会儿再说。”
“好的好的。我没事,他瞎说的。”老乌在众人的目光洗礼下有些难堪,讪讪坐下后没再试图起身。
强硬挤进属于别人的旅行,确实让我偷到了些许轻松快乐。陌生、新鲜,正是我此刻最需要的。我收回目光将耳机挂到原位,降噪一开,汽车内的噪音和其他轻浮、庸俗的东西立时被排除在外。出于未知心理,我选择了费舍尔某场演出的录音专辑作背景音乐,盛大的交响音乐在某个时刻停顿了两秒,息屏通知栏上闪过来自王天润的信息。我恨自己的眼神太好,随便一看就读完了内容——对面问我,是不是改机票提前回国了。王天润当然会知道提早退房的消息,我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开的他的控制。往好了想,这代表他对我的上心,是不是能为此生出些安慰来?可往坏了想——我总忍不住往坏了想,王天润有多希望我能变成替他事业添彩的那朵缀在树梢尖的花,在必要的时候,他就会以同等分量的希冀——压迫我俯身趴跪成为一段,在下行路上助他平稳落地的台阶。除此以外,不该有别的念头。人都说只有年轻一方才会需要踏脚石,我也以为自己才是踩着他爬的那个,实际情形却不尽如此。这样老谋深算的一个人,我不光在计划抽身离开他,甚至还想在跑远前利用机会摆他一道。绝对天真的愿景。
是我错了吗?还是这段关系的黏合剂已变得过于强势?
和王天润一起在苏黎世度过的那个夜晚,即使明日的胜负未定,他已提前作好把泡泡工厂现任管理层解体、再由我空降接手的计划。我问他为什么?是现在的团队做的不够好吗?他却说:“我容许他们搭上我的船行一段路,已经很宽容了,我讨厌被人骗。”
任远劳已经把白胜假造 AI 试图熬到八百万期权的真相全部告诉了他。那时胸口、后背因性爱而生出的汗水还未完全风干,裹在羽绒被里,前后的透凉夹住我的心口,逼得一颗心脏跳动如擂鼓。这是一个决定他人命运的时刻。我对于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判定很肤浅,那就是看他能左右多少人的命运,我曾把对成功的遐想寄托在王天润的身上——他是一个比我父亲更加贴近现实的活样本,像一个开天辟地的神,指挥重塑渴望的形状,他说该如何那便如何,该如何做,那便如何去做。藏在他的影子底下,顺着他的手臂弧度挥动,一切如此轻松。此刻,我终于又通过他间接体会到这种刺激了。那让我恐惧也让我激动的时刻。我听见自己说:“如果……他们被赶出去之后不甘心重组新公司,那怎么办?”
“人嘛,走就走了,他们生产的一切都属于集团。我准备把现在这个泡泡工厂分出去,他们敢组团队,你就用他们做的程序把他们挤死在初创期,有难度吗?”
“没有。”我是很乐意在王天润的大旗下做些坏事的,身后的塑像太过高大,罪恶荣耀集于一身,没有人会因此而怪罪我。
“不用紧张。我根本没对这个 AI 报有期待。”王天润笑道。黑暗中一双热手抚过我的肩膀,我赶忙将肌肉放松,趴到枕头上一动不动。男人的声音因为困倦而变得沙哑,“你就当拿过来随便玩一玩。这是我送给你的圣诞礼物。”
我问:“嗯……为什么是圣诞礼物?”
我想,是因为这段关系有可能会在圣诞节前结束吧。
王天润没说话,只是用手指撩开我额角的碎发。我不由对自己的计划产生些许愧疚,但更怕有丁点异样被他察觉。他说他讨厌被人骗,如果失败了,我又将面对什么样的惩罚呢?那一定不是撒娇卖乖甚至脱光衣服任他玩弄就可以平息的。我在他的影子下祈祷,但愿那天永远不会来临。尽管内心无比讨厌矮化自我的行为——从他带我入公司的第一天、第一年开始……他的暗示,他的惩罚与奖励我受够了——可实际上,七年足够养成路径依赖,我还是忍不住捧起他的手亲吻指节和手心,带着悲哀的渴望将他的手指含入口中,顶在牙面和口腔内壁之间。好像这样子,信心就会平衡心底的虚弱。身体还未恢复到前半夜的状态,王天润又从我的屈服里获得了新一重的乐趣,最终允许我拥抱他步入睡眠。
这样谄媚的我,真是受够了吗?
音乐再次停顿。又一条信息,我不想去看,但过了几秒还是不敢不看。划开手机,发现传简讯的不是王天润,是林彧。谁?林彧?刻板的、后梳着头发,带着薄汗的林彧。活在我肉体上的男人。天呢,我都快忘了他了。刘正毅说会帮我支开他,让他忙到没空骚扰我……现在是时间到了,封印解除了吗?我对刘正毅的允诺总有种迷之信任,觉得他能把我玩弄于鼓掌,对付林彧想必也是有一套的。好一段日子不见我都以为他成功把林彧撵出厦州了。事实上,林彧没有那么厉害,刘正毅也没他自己想象中那么厉害。而我呢?我其实对那些在精神上能压制住我的男人毫无办法,又不甘于此,忍不住想要把信心和尊严从那些压制不了我的男人身上讨回来。我将这种行为描述为“弱肉强食”。这么一说,复杂的关系一下就变得天经地义起来了,对吧?
哎,林彧竟也挑了这个时间问我人在哪里,在我装死了十几分钟后,也不墨迹了直接打过来一通电话。滴滴嘟嘟的音乐声在车厢里唱起,前边的皮匠掀开帽子看我。我忙把手机关机,从挎包里掏出和刘正毅单独联系用的备用机,用针顶开卡槽,哆哆嗦嗦用指尖粘下手机卡。板起脸紧张万分,心里不由骂骂咧咧起来——干,这什么鬼设计一点都不好插,我还是双卡双待的更加完蛋了——才转移到一半,车轮子越过土坑,飞了半秒重重砸地,还没指甲盖大的芯片在我的惊呼声里飞了出去,划出一条白色的弧线,掉落在过道。
我伏在软凳上寻找芯片的踪影。有人问怎么了,我没理,只顾着找自己的电话卡,等拍打肩膀的力道变强,变为直接捏住我的胳膊摇晃,堪堪回神,皮匠正扶着椅背站在过道里,摊开的手心举到我面前,上边乖乖躺着一粒芯片。我松了气,爬起身从他手里取过卡片,捏在食指和拇指间,在车厢的剧烈晃动中一遍遍试图将其固定在镂空的金属卡槽内。
“你这么年轻,手怎么这么抖啊。”皮匠坐在过道对面的椅子里,侧着身坐,一支胳膊撑在前座的椅背顶,目睹了我帕金森级别的操作,忍不住吐槽。
身子虚,行了吧?我泄气地向后一躺,说:“那你来!”指尖一松,反面的副卡也掉了下来。
皮匠回头瞥一眼,确认同伴都在睡觉后,起身坐到我旁边,接过两张卡,完成不受颠簸影响极轻松地用指腹一推,装完一只手机,又用更快的速度装完第二只手机。他的手指,尤其是食指尖有一层长期做手工活留下的薄茧,指甲剪得圆钝嵌在肉里,使十根手指头在视觉上变得粗宽,这样一双手做出灵巧的操作,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我感叹:“要不然你是皮匠呢,手就是稳啊。”
皮匠把东西递给我。客车穿越山岭驶入隧道,长久的黑暗来临,如果他一开始是想帮我搞完手机就回到自己座位的,被长长的隧道打了岔后,也改变了主意。毕竟逼他坐在这个既尴尬又冒失的位置的,不是别人更不是他自己,是闽南八山一水一分田的雄奇山麓。要怪就怪这山和水,怪这隧道。
在一片山头的腹地横穿而过,片刻的光明后紧接着钻进下一片山头的肚子里。老乌独自坐在第一排,额头抵着玻璃大张了嘴巴睡得正香。
“你不困吗?”我问。
皮匠淡淡说:“还好,这个点我一般都在喝咖啡吃下午茶,习惯了,不喝也睡不着。”
“你要不要吃糖?下午茶没有了,咖啡也没有了,来块巧克力打打牙祭吧。”我拆出一包在免税店购入的原味巧克力,掰一小片下来,想到他的年纪又补充道,“你……你能吃糖的吧?”
“怎么不能吃。我身体比你还好呢。”皮匠不以为意,接过糖果塞进嘴巴。他的牙口似乎也不错。
望着他忽闪忽闪的镜片,发根若隐若现的银发,还有因用力咀嚼而清晰起来的咬肌——几乎因观看他进食而感到欣慰的我,不知为何自动跟了句:“真有那么好吗?”我本意并不是想调情,只是话说出口自动变了味道。没办法,浅薄的人,说不出什么好话来。皮匠停下咀嚼,意味不明地看了我一眼,反倒让我不自在起来。
把巧克力丢进嘴里,嚼了两下,耳后有刺痛,扭头,白老师和他的女友团一个个睡得东倒西歪,刚才一闪而逝的窥视似乎并不存在。灰发胖男人在我的注视下翕动嘴唇,勉力哼出一声细小的呼噜,我笑了,回过头不再强人所难。
“好吃吗?”我问皮匠,吮过黏有巧克力粉的手指。
“……好吃。”他的声音发紧,目光在我的唇边徘徊。
手机在大腿上震动起来。亮起的屏幕上是一串虚拟号码。刘正毅。犹豫了会儿,我没接通。电话在时间到后自动挂断。
骤亮又骤暗的脸在光影变换间不再沉稳,皮匠看着我和一个电话较劲,甚至神色再没了先前的愉快,不确定又开始在他的身上蔓延。
终于,他问出了一句越界的话:“怎么了?”
“没什么。”我笑着抬手,在皮匠微妙的强自镇定的躲闪下,撩起他脸庞一侧垂挂的眼镜绳,打着圈绕在食指上。灰色中夹着墨绿色丝线纹路,可惜没有弹力,和刘正毅的不一样。
或许真的发生了的更近一步,不知道要不要放进正文
“下一段隧道有点长。”我说。皮匠不明所以,却在新一轮黑暗中对骤然贴近的呼吸与亲吻表现出惊人的适应。或许半天相处下来,他在不知不觉间对我怀揣了某种模糊的不可言说设想,而我也确实让他的设想落地为现实。是以灼热的呼吸在鼻尖抵碰时双方都为之有些退缩,吮舐含着焦虑,激烈得有些过火。
“司机师傅,能不能开个灯啊,我的眼镜掉了。”车厢尾,白老师的声音传来。身后悉悉索索的布料声响起。我暗骂一声,飞速收回已探到身旁人大腿内侧的刚摸出来形状的手,等车内照明亮起,已摆回原来的姿势,倚窗撑着下巴手背不着痕迹地抹了抹嘴。
“这款巧克力味道确实还挺不错的。”我低声品评道。
“嗯。甜了点。”皮匠应了声,低着头用衣袖擦抹摘下的眼镜,风轻云淡,等面上的潮红悄然褪去,一切异样全部平息,老乌也睡醒了开始困惑地张望,寻找消失的老友,他才终于起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