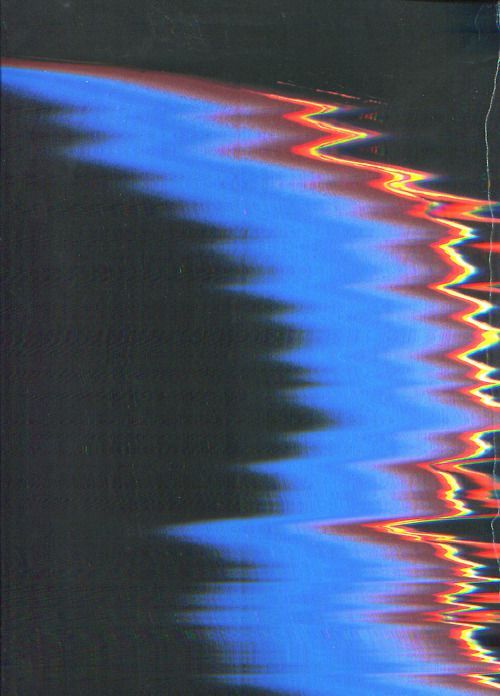乐园(1)
快速目录
林彧:青春费
走到地下停车场时我便感觉有一道目光黏到我的后背上,于是加快速度走向停车位。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办公室为我准备了惊喜蛋糕,切下一块就要双手送去蛋糕微笑感谢一个人,就这样,我一共感谢了十五位同事,感谢他们的支持。这是一个领导的风度。结束社交的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溜到楼下开车,衬衫、西装裙上还粘着金色的彩带碎,我启动了车子却又开始犹豫是不是直接回家。丈夫和孩子一定也为我准备了一系列的仪式,又是一座蛋糕,又要唱一遍生日歌……我自认为这种消极态度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有了家庭之后,父母的生日其实也只是孩子玩乐的藉口,寿星本人并不如何重要.
正趴在方向盘上发呆,手机震动响了,锁屏的白光照亮我的脸,闪出的信息也让我心头一跳。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给我发送了生日简讯。我几乎想把这条信息打印下来装裱放在办公室桌头,然后大笑,哦,哦!这可是我半年多攻坚克难的成果啊!我确定,这才是我真正的生日礼物。爱死了。
没一会儿同一个聊天框下又跳出信息:方便吗?
我连忙解除手机的静音。微信电话的铃声响起,等了两秒我便接通了它。“王董……”我听到自己故作矜持的紧绷声音。我太欣喜自己的成功——关系的突破将会在不久的未来为我职业生涯添薪加柴,即使代价是做另一个人的地下情人。呵,多半也做不成情人,不过是玩上一段时间,也不知对面什么时候就嫌腻了……但没关系,有一个董事在后边撑腰,这次的升职板上钉钉。现在是笑贫不笑娼的年代,能找到路子也是一种本领,要看懂眼神交递下的意思,要识情识趣,也要有先踏出一步的勇气,还有放下身段的决心,可不是本事?我太欣喜自己的成功——以至于没有看到车窗外已经站了一个男人,他穿着黑色衬衫打着领带,鼻子上架着副细眼镜,正眯着眼睛朝里看,也不知道看到多少。我一扭头反倒被车玻璃上倒影出的,惶惑与谄媚交杂的面容吓了一跳。那是我自己的脸。
挂了电话,摇下车窗,我惊奇地扫视着窗外男人的脸,不无惊慌地低声叫道:“你怎么在这儿?不是和你说过不要再来找我了吗?”已是夜晚的八点,作为国内头部的互联网公司卷王层出不穷,车库里自然还停了不少车,所幸没有人在这片区闲逛。
我警觉地向电梯口张望,问:“你怎么进来的?”
林彧只是微笑:“走进来的。想请你吃顿饭,给个面子好不好?亲爱的?”
这个男人……他跑到公司楼下堵我,真是找到了我的命门。要是在别处我一定让他从哪儿来的滚哪儿去。我怕他闹事,只能点头。公司经常裁员,闹事的人很多,所以一有风吹草动保安就会过来。
林彧拉开了我的车门把我牵出,贴心地帮我锁上车,接着无比熟稔地将胳膊环过我的肩膀,不顾我的嫌弃将散发古龙水香气的脸凑到我的耳边,嘴唇紧紧贴住我的耳垂呢喃:“生日快乐啊,小高。”酥麻顺着后脊梁往上爬,使我半个身子不受控地歪向在他的怀中,可我不肯认输,将一双高跟皮鞋踩得啪啪直响,恨不能一鞋跟把他的脚趾踩烂。侧脸看到黑色的衬衫前晃荡着一块挂脖的工牌,扯过来一看,照片和名字都不是他,也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居然真的能刷开大门的第一道门禁。
不情不愿上了他的车,本来想坐后边但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最后坐到了副驾驶位。驶出公司后,我看着林彧把车开上高架,咸腥的海风透过车窗的小口子吹起我额前的发丝。身边人不断瞟我,可我偏不理他,直到他伸手到我的裙子下摆才正过脸,拍掉他的手,厌恶道:“你干嘛。”
他的手很快,指尖捏着一片银色的塑料彩带,让我看过之后抬手往车窗外一丢,彩带瞬间就不见了。林彧操着他那口很有台味的温柔国语对我说:
“你过的还好吧?”
他怎么好意思来问我过得好不好?从我十五岁第一次在学校外的小巷子里遇到他开始,花言巧语使着上不了台面的手段从我家抠出多少钱来?能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盖两三套别墅了吧!利用我难以启齿的心理疾病,把我当作提款机玩弄,甚至偷偷换掉我服用的药物……
“要你管呐,少来装熟。”
“咱们两个的情分……怎么会是装熟呢?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多愁善感起来,这几年我一直在想你。有的时候会开车路过你的高中,我就想,哎呀,也不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是不是还像以前一样总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你爸爸过世,我还去殡仪馆吊唁呢,但你那时候和男朋友站在一起哭得很伤心……我就不好意思去打扰了。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就要和我断掉,但我们以前在一起是很开心的嘛。”
怎么还有脸提我爸爸。来殡仪馆是想来看我的丑态吧!那天到场的还有爸爸的小老婆和私生子。被亲戚们悄悄排挤的我只能站到外人那一圈去,上去说追悼词的另有其人,怎么看最后继承战的赢家都不是我。最先断连的人明明是他。我简直快气炸了,连忙拉下车窗透气,怒道:“你搞清楚好不好大叔,以前是我包你啊……你别自作多情。”
林彧的脸上飞速闪过薄怒,我在心中冷哼,眼看着他重新挂上委屈和故作宽和的笑:“你个小姑娘,什么叫你包我啊?不要说得这么难听。”
我还有更难听的呢。管你说什么鬼话嘞!我直截了当告诉他:“你来要钱我也没有了。我现在都要给别人打工欸。”现在轮到我去舔别人的鞋面了。
“你在前边路口下去,把我放下来。”我命令道。
“距离我订的餐厅还有五公里。等一会儿就到了。”
“快点放我下去啊!”
他不理我,我直接解开安全带拨开车锁,拉开车门作势要跳车,滴滴的警报声下,门才开了一条小缝就被林彧侧身强行关上。骂了声“干”他明显忍无可忍了,恼怒、震惊、颇为仇恨同时也颇为怀念地瞪了我一眼,咬着牙无奈把方向盘一转,进了匝道。后备箱有什么东西倒了。我满意地嘻嘻笑起来,享用着他的恨意。
下了车。他又叫住我,打开车盖,后备箱里边铺满了粉白色的鲜花和紫色点缀用的气球。只是鲜花被急刹和剧烈的拐弯后东倒西歪。林彧一头扎进花堆里,半个身子埋在里边翻找着什么。
“你——”我竟一时语塞——三小啦!藏在花堆里的电源被按响,穿插在气球中间的黄色星星灯亮起。搞什么鬼啊。林彧扶正眼镜倚在车边上对我笑道:“不想吃饭就算了。祝你生日快乐。”
我张嘴刚要说话,电话响了。我警觉地瞥了眼车边的男人,踱步着远离他。
“喂,嗯……已经下班啦,还没到家哦。谢谢你今天的水果蛋糕很美味。嗯真不好意思,还要你费心做这种小事……好,注意休息哦,不要太辛苦了。好”
才挂掉,又一通电话打进。
“我在路上啦。还有……”我抬头朝四周望了望,寻找着标志建筑,下了柏油路再走十米就是沙滩,黑夜中海浪正拍打沙粒,该死的林彧给我拉到哪里去了,只得叹气说,“还有呃半小时到家吧。妮妮饿了就给她切蛋糕吃……吹什么蜡烛啊,没事的,让她先吃吧,太晚了不好消化。”
挂了电话,见林彧用一种别有深意的眼神望着我,他的敏锐足以判断出我两通电话的不同之处。我理直气壮地回瞪他:最先教会我左右逢源的老师不就是他吗?平时互相假装不认识,可影响真的不存在?林彧自以为标准的那口国语连带着我口音本不重的普通话也变了味。同学开始说我骂人也像撒娇。老公说我叫人也是嗲的。真的只是口音吗?是那些属于林彧的骗人话术,还有他做作的热情,拆散打乱,重组变成了我的语调。我只是不知不觉得了他的真传。
又在多年之后,走上他行过的老路。
可我卖的是青春费啊,我的身体、我的温柔,它们值钱呐!林彧嘞,他值什么钱?我遇到他的时候他都三十好几了,也就我病急乱投医肯买他的帐。
如果看出来我在干什么,他也假装不知道,耸耸肩感叹说:
“小高,你的温柔现在都不肯给我了。”
干……我对他什么时候温柔过?我会在情绪失控的时候打他的脸,踩他的手。抑郁、焦虑、种种青春期的不安和骚动让我无时无刻不在渴望性,还有性带来的片刻逃避,以至于我在课间躲到厕所里去自慰,一次又一次和男同学、校外的混混、发廊小弟在树丛里、小巷深处发生关系。我让我的家庭丢尽了颜面。心理医生说我是“性瘾症”,需要疏导和服药,但这三个字本身就是罪过。林彧某天在小巷中捉到我的丑态,那时我正被压在一摞啤酒箱上。
“我还以为有人欺负你呢。”他说,捏着手机好像要报警一样。
“我给他钱了。”我叫道。“你别说出去。我也可以付钱给你。”
金钱就是我和他之间的通行证。他告诉我我并没有得所谓的“性瘾症”,我只是学习压力太大了,疏导一下就能变回正常人。我并不相信,但我爸爸相信了他,总之,只要我得的不是这种不要脸的病,怎么都行,一定要治好,多少钱都要治好。他的治疗方法就是带我前往一栋隐秘的房子,每半个月一次,很多男男女女会聚在一起聊天,等到时间差不多了,各自挑伙伴过夜,如果想要多人组队只要互相同意都是可以的。
这什么治疗嘛,这不就是淫趴?
在休会的时间里,大家都要尽量控制性欲,这样每月两次的集会就会变得尤其珍惜。我哪里管那么多,只要有的发泄就好啦,我才不会戳穿这个骗局。每月两次肯定是忍不住的,我只好偷偷去找外边的人,就像以前一样。林彧发现了告发过我一次,爸爸很生气命令我要听林老师的话,不然就不给零花钱。呵,林老师?
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我就只好去找林老师了。他一开始还假正经,说不可以。我早有准备包里倒出一打现金,丢给他说:“干一次五千块。”
“一万块。”
这老东西。
我翻了个白眼。“……成交!”
他的体能很好,比我们学校的长跑冠军还要好。但他不是一直都在,每个月都会神秘失踪好几天。我找不到他的时候无事可干,只能不断自慰解馋。有一次他失踪了足足一个月。等到他再出现的时候,我给了他五万,说:“加四万块,我想玩点刺激的。”只要是钱他都要赚。贪财的老东西。
我根本不想玩什么 sm 的,我只是想找个名义打他、虐待他而已。看着他鼻青脸肿,被玩到尿失禁,我发现我对于性欲的需求降低了。林彧这个假医生或许说对了,我只是需要排解压力。
不知是不是榨了太多次,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已经不太行,但从我家持续榨取的资金一定很可观。那年爸爸也去世了,我从遗产里得到的不算多,可对比普通人也绝对不算是少。溜到国外后,参加过几次 party,兴趣缺缺,家庭解体后我竟然一夜之间从性瘾者变成了性冷淡者。那一刻我清楚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好像我的青春突然就结束了,怅然的同时还有解脱,我终于,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删除手机里备注为“林彧”的号码。这个捧高踩低的卒仔该是带着对我和我爸爸的厌恶消失的吧。
哎哟,糟糕,我怎么因为自己目前处境的相似,对他升起同情来啦。
“我叫个车啊。”我终于好声好气对他说,先前的话假装没听到。总不好纠正他说,林叔你老年痴呆啦,对你温柔的可能是别的哪个女孩,搞错了啦!
“还有多久到啊。”
“……十八分钟。”天啊!
“陪你散散步吧,反正还要等一会儿车才来。”
我们并肩朝沙滩走去。
“你离开之后大家都很想你。”林彧插着兜望向海面。
“谁啊?”
“‘乐园’里的那些人。”
那些和我聊过天、睡过觉的各种各样的人。
“他们都好了吗?”过上正常的生活了吗?林彧总不会也偷偷换过他们的药吧?不要那么残忍。
“有些回家了,有些还在。”半响他才提议,“你要不要回去看看?”
我歪头皱起眉看他的鬓角,严肃地对他招手:“你过来。那边有个东西——”
林彧犹豫一下,疑惑地凑近我低下头。我极迅速地从他脸上扒下那副装模作样根本没有度数的眼镜,使足力气朝着大海奔了过去,中途因鞋跟崴了下,一甩双脚,两只皮鞋飞到后边去,冰凉的海水冲刷过光裸的小腿。镜架划出一条弧线,扑腾一下掉到海中。
“干霖娘啦!”我生怕自己的声音又被听成撒娇,喊得再大声四个字还是被海风吞掉一半,“就不肯放过我!你有本事游过台湾海峡去捡回来。”身后的林彧正在弯腰捡起我的第二只鞋子。
我率先赤着脚走在前面,沾了一脚的沙子,林彧跟在后边。
电话又响:“小姐,车抛锚了,你另外叫辆好吧?”
我拉开林彧那辆黑轿车的后车门垂头丧气坐了一会儿,等他走近跟前缓了好一阵才说:“好啦,你找我是想怎样?要钱还是要人?要不要干,干完把我送回家。”
我站起身故意去解短裙的拉链,然后撩起裙摆让他看我的大腿,林彧还是一脸高深。呵,还不高兴哦,如果是不愿意,那就去开车啊?又不开。看着女人脱衣服无动于衷真的很没礼貌,所以还是要钱咯?我停了手把拉链重拉上捞起手提袋掏出钱包,数了数,把仅剩的两千多块现金取出拍到驾驶座旁的扶手上,希望这点钱能让他感到羞辱:“好啦好啦,老样子,我包你啦。你当回司机把我载回家吧。”
两千块他竟也收了!他还是厚脸皮,可也混的实在不好,比我学生时代还要差。
我缩回车后座上,谁知林彧不去开车也跟着钻进后座,带上门,一边开始解裤子,一边掐住我的脸开始亲来亲去,掐得我脸颊生疼。“诶!”抬手推他纹丝不动,反被压在皮座椅上,我一下就知道他是动真格的了便不敢撒泼,怕他把我的手扭伤。他以前干过这种事,青紫的伤痕都是小事,有一次逼急了甚至把我的胳膊卸下来。林彧找到空档将手伸进裙子里去,摸到两腿之间,比撒哈拉沙漠还干的那片地方,抬起头满脸惊讶问我:“我还以为你假装……”
又问:“那你和你老公怎么生的小孩?”
性欲衰退又不是切了子宫,真是懒得理他,要个孩子不容易,但也没那么难。林彧压着我眼睛里闪着犹豫瞄向我的胸,我猜他是想要不要再来点前戏什么的,催他道:“直接拿润滑液吧,你车里有没有。”
话说回来,怎么他遇到我这种扫兴的对象也是兴致不减的,非做那事不可吗?
林彧直接拉开我的手提包,不顾我的抗议扒拉来扒拉去在各层里找到一支润滑液。这家伙,我望着车顶棚感叹,是不是有点太了解我了。抹完,趴上来的时候,他还特意严肃地叮嘱:“你不要抓脸和小手臂,明天我有正事。”话音没落就进来了。
我看他脸上渐渐红起来,气喘吁吁的,动起来后居然对我说:“……下边好紧。”
“你多久没做过啦?”我问他。
他转转眼珠想了两秒回:“好久了,半年多吧……八个月。”
我不想告诉他,就算是这样,他的性生活频率比我和我老公的做爱频率还高些。对于夫妻来说,一年只做一次好像真的很过分。
“你……好歹给点反应,好不好?”他喘着粗气说到最后几个字笑了起来。
“对不起哦。”我舔着下唇,闭上眼,“你努力一下……我再感受感受。”
林彧像了解我的内心一样了解我的身体,所以他反复戳弄的地方让我感到一阵熟悉,那里曾是我的死穴,曾经只要一碰到那里,我的嘴巴就会像个疯子一样喊叫,身体却像脱线的木偶动也动不了,每到这个时候林彧就会像操线的偶师,漫不经心地将我搓揉摆弄着他想要的模样。曾经确实是那样,现在那儿只是一块平平无奇的软肉。怎么会这样呐?我扯住他的领子把他的嘴唇拉到嘴边啃起来,试图用这种行为唤醒一些年少的激动,但我真正品尝到的只是另一个失意中年人的乏味嘴唇。以前我多少对他有些喜欢,会觉得他如此不同。他的残忍、漠然、虚假的礼貌都富有成熟魅力,它们隐藏得并不深。林彧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很遥远,可他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又太近了,每天返工身边都充斥着这样的人,连我自己都不外如是。我的意趣转移到了未知的地方,跟着跑路的还有我的 G 点。
“你……”
“别说话。”我轻声对他说。在脑子里,我想把他勾画成另外一个男人。他应该坐在昏黄的落地灯前看书,看的该是萨特或者是叔本华吧?探讨人的存在或是别的终极问题,总之不会是《教材全解透:高中历史》还有《高考宝典》。当那个男人的形象不受控制越来越趋近于我那在高中任教的丈夫时,我发出了一声哀叹。林彧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把脑海中的落地灯取走,换成昂贵的橡木办公桌,上边摆着极有设计感的台灯。落地的玻璃窗被灰色的窗帘盖住,顶层绝佳的位置能便览奥传司大楼里各层职员挑灯夜战,那人将我推到书桌边上,塞进办公桌下的那个空间。双膝触到柔软的地毯,一只手伸到我的耳后抚摸的手法仿佛安抚自己挑剔的宠物猫一样,只要我稍稍偏头,就会看到浆洗雪白的衬衫袖口,还有上边点缀的那颗 Deakin&Francis 白珠母贝袖扣。半米之外的身后来来去去好几拨人,我神志不清地藏在桌下尽心地完成我的服务,听着这些比我还要高上好几级的大领导们战战兢兢说着我不该听到的信息,飘飘然,飘飘然,好像我也在某种程度上压了他们一头似的。多可悲啊。书桌下很小,我得避开隔板,不能弄出一丝声响——我保持着头颅的位置,悄悄地,极慢极小心地,给予麻痹的双腿以微弱的释放——啪!
腿踢到了车门的扶手。我一下子又回到了林彧那辆逼仄的日产轿车里。他骗了我家这么多钱,到最后还特么开了辆小几万的二手破车!而我还在这辆破车里和他苟合!怒火在我的心底燃起。
“来感觉了哦?”林彧笑道,一挺腰身,将手臂撑在车窗上,将我的双腿捞到肩上,黏腻的水声随动作响起。
“啊——”感受到体内侵入的加深,我终于发出了今晚第一声由衷的呻吟,抬手胡乱地想要抓个东西,又想起他先前说的不准抓手臂和脸———干……我也只好把手撑在头顶,抵着车门免得被越来越激烈的运动搞晕。
像被钉死在座垫上,又像没着没落地在气味深重的狭小空间的漂浮,一上一下。林彧解开我的衬衫衣领,将胸罩向上一拉,捞出一只完全不同于从前的因哺育而丰盈的奶,将脸挤到衣领中间去嗅去舔舐、撕咬。他大喘着气,额角的青筋跳动,倒在我的怀中像一只脱力的却还要继续挣扎的困兽。我和他紧紧抱在一起,脑子里闪过一连串的不重复的脏话,可我还是不自觉地环着他,与他紧紧地、紧紧地抱在一起。
在释放的一刻,他离开了我的身体,将白浊洒在我的肚脐之上。好烫啊,要烫伤了,我忙不迭拉出一片湿巾将他的痕迹擦除,仔仔细细一点不剩。林彧撑着头对着大开的窗户,让流动的空气散去不洁的气味,推开车门出去站在马路上重新系好皮带。歇了一会儿终于坐到驾驶座上启动了车子。终于。
发动之前林彧拉下遮阳板,取出一柄白色的塑料梳子递给我。“理理头发。”他说。我嫌弃地摇头,拿出了自己的气垫梳。林彧不以为意地用小白梳整理起自己的发型来。
“有空去植个发吧。”我意有所指地瞟了眼他的发际线。
“哪有钱呐。还是说你资助我?”
“那你还是去理个光头吧,五块钱就够了,就从车费里出。”
林彧呵呵笑了一会儿。
到了小区门口。林彧又叫住我说:“闲得无聊就出来玩。你知道地方的。”
“那是你的地盘吗?一到那儿都找不到你人影儿。”
“你真想在那儿见到我?”
我回想起曾在那儿见过的形形色色的人,各个都比林彧有意思。摇头。
林彧神秘地笑着,朝我挥挥手说了再见。
回到家,客厅茶几上放着已经切动的蛋糕,走进家还得小心不要踢到丢得到处都是的玩具。儿童房房门紧闭,丈夫不见人影,多半是陪小孩睡了。我取了衣服溜进浴室,飞快地冲刷走林彧的剩余气味,此时我才发现自己的乳尖不止是泛红……都被咬青了。我靠林彧这老东西……
“你的毛巾晾在阳台没拿。”
卫生间的门不知何时被打开,门后是一张看过千万遍的脸,吓得我手中的莲蓬头都摔到地上了,赶忙侧过身抱住自己的胸部。
“不好意思。”武文陆尴尬地低下头递毛巾,纵使是夫妻关系,但他看到我的裸体,就像看到一个陌生女人的裸体一样。我为自己一惊一乍的行为感到后悔,害怕刚刚不经意间释放出的拒绝对他再次造成伤害。尽管我对他的兴致缺缺就是最漫长的凌迟。林彧的卑鄙让我联想到自己的不堪,有武文陆这样的人作丈夫,也时刻映衬着我人格的矮小。
断又断不掉,好又好不了。这样的生活也不知有什么意义。
洗漱完划开手机,在“王天润”三个字上反复游移,斟酌着发送出了晚安问候。五分钟后得到满意回复。很好。
“还有两片蛋糕我放在冰箱了,明天要不当早饭?”丈夫在床的另一头说。
“嗯。”我漫不经心答复。
关了床头灯,我还是决定凑过去给了枕边人一个脸颊吻。“早点睡啦好累啊。”说完我就阖上眼立刻陷入睡眠,错过了他那句迟到的“生日快乐。”